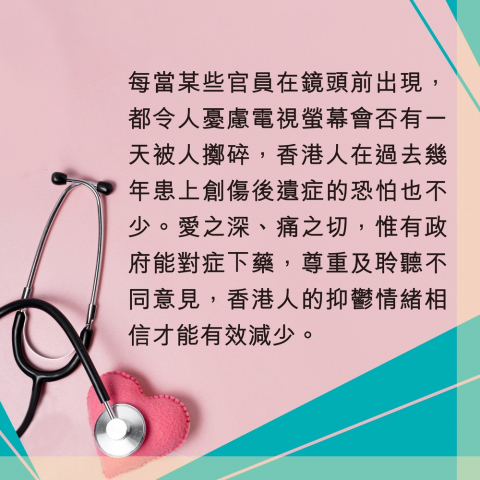蔡志森 | 明光社總幹事
| (獨立媒體.2024年7月9日) |
城市大學的團隊在2020年至2023年間,透過問卷訪問共4002名中小學生、家長及教師,發現有近三成小學生認為自己有中等程度或以上的抑鬱,中學生更近五成。而中學生的家長超過三成有中度或以上程度的抑鬱,小學生家長則有約一成。調查結果相當驚人,不過就要小心解讀,首先因為大部份時間橫跨疫情的高峰期,而據報道所謂抑鬱的程度是自己認為的,大家對抑鬱症的了解和定義是需要進一步分析的,這與開心指數不同,因為開不開心自己可以判斷,但自己是否抑鬱需要更多專業的協助才能更準確地判斷,否則只會淪為一個主觀的形容詞,產生不必要、先入為主的錯誤觀感,正如當過度活躍、專注力不足這些名詞普及之後,很多人(包括家長)很快便會對一些好動的孩子加上過度活躍的標籤,更令人憂慮的可能是會立即想辦法壓抑子女的好動性格,彷彿活躍就一定是不好的事。在香港這個人口密集、市區內公共活動空間不足的環境,許多兒童平日困在家中只能打機和上網,若連到了室外也不活躍反倒應該令人憂慮。
另一個令人憂慮的現象是,當發現有學生和家長自認為抑鬱,大家很快便將結論跳往教育和考試制度的問題,彷彿減輕了考試壓力就能減少抑鬱,其實香港人抑鬱的原因還有許多,疫情帶來的生命和健康脆弱的憂慮;經濟未如理想帶來的財政壓力;社會撕裂和政治壓力造成的憤怒;移民問題帶來許多感情上的不捨,小朋友亦無法逃避;居住問題狹窄令成人和小童也有很大的壓逼感;還有許多曾經擁有已漸漸失去,例如選舉與被選權利的大幅收窄、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紅線處處,批評政府和施政的風險大增,令人不敢暢所欲言表達真正的感受和意見;一些普通法的基本精神逐漸改變,例如未被定罪前假設無罪、疑點利益歸予被告、不應未審先囚及延遲審訊等等;面對這許多的社會問題,教育問題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壓力來源,香港要正視的又豈只教育問題,看看身邊的朋友,離開的固然有滿腹牢騷和擔憂,留下來的也有不少經常出現情緒波動,每當某些官員在鏡頭前出現,都令人憂慮電視螢幕會否有一天被人擲碎,香港人在過去幾年患上創傷後遺症的恐怕也不少。愛之深、痛之切,惟有政府能對症下藥,尊重及聆聽不同意見,香港人的抑鬱情緒相信才能有效減少。